发布日期:2025-07-03 14:25
来源:www.bdal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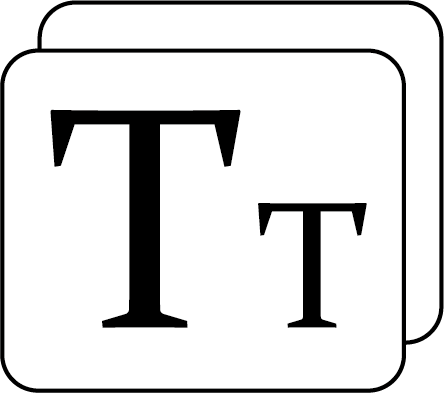 字体:
字体:
□贺东杰
“胡同”一词来源于元朝时蒙古语“水井”的变音,有人必要有井,有井处才有人居住,胡同就是为市井生活而生。
我从小生活在胡同里,胡同生活才是生活的样子。
小时候县城里没有几座楼房,胡同密布,我们这些就知道疯跑的孩子天天在大小胡同里出溜。那时的胡同就是我们的游乐园,从南头到北头,从初一到三十,从春天到冬天,风霜雨雪,随时随地开玩,什么也挡不住玩的脚步……
胡同里有无忧无虑的童年
那时候孩子多,放了学书包一扔,招呼一声,一大群就去玩了。无需任何成本的“藏迷糊”简便易行,“官打捉贼”趣味多多,大冬天的在外面挤摞摞靠暖和,男孩子们时不时来上场“战斗”,单腿站立,另一条腿用手扳着,搭在站立的腿膝盖处,蹿蹦跳跃,挑砸撞压,以击倒对方为胜为乐,或单挑或群战,胡同成了我们的战场,我们都成了拍马舞枪的大将军。
略微有些成本的游戏是挑冰棍签、砸杏核、扇四角,也只是需要在大街上捡人家扔掉的冰棍签、杏核,搜罗些破书旧纸,然后宝贝似的收起来,谁的多那可是光荣至极的事。成本昂贵的就是“滚铁环”“打皮了猴”“弹球”这几样,得用到粗铁丝、木头和滚珠、玻璃球,拥有这几样是很值得炫耀的事。至尊之物就是木头手枪和铁丝枪,那需要家里大人是能工巧匠,有“枪”的孩子绝对是孩子王。
我们总能找到玩乐的项目和伙伴,玩着玩着就长大了,可长大之后发现快乐并没有随着一起长大。
胡同里有四季分明的时光
在楼里住久了,我发现对四季的感知能力都差了,只能靠手机里的日历来判断。
住在胡同里的时候,和小伙伴们跑东家串西家,春天发现二蛋家的杏树开花了、黑子家的桃树长出花苞了、胖墩家的榆钱该捋了、猴子家的香椿能吃了……槐花开了枣花开了春天过去了。夏天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白天听着知了“吱吱”叫着,傍黑捂上几只蚂螂,黑了去逮知了猴……杏熟了、桃熟了、桑葚能吃了……哪一家的果树都会被光顾,内应大多就是那家的孩子。
秋天里葡萄、石榴、枣……也早就被我们惦记上了,那时能吃上一个半个感觉真甜,真好吃!大冬天孩子们也在屋里闷不住,下了雪也要在外面打雪仗、堆雪人,常常是棉袄、棉套鞋湿透了才跑回家。
那时胡同里有附近村子里的小姐姐小妹妹在一场春雨过后到城里来卖曲菜,柔柔细细的声音送来了春天,“卖小鸡嘞”的吆喝声和小鸡崽的叽叽喳喳送来了春天,“小豆冰棍儿、奶油冰棍儿,三分五分”送来了夏天,“辣椒、咸菜、臭豆腐”送来了秋天,“大糖枝、糖葫芦”送来了冬天。
货郎车的拨浪鼓、卖豆腐的梆子声、“磨剪子嘞,抢菜刀”的悠长吆喝声……行走在胡同的商贩送来了春夏秋冬,送走了春夏秋冬。
胡同里有烟火人情的生活
低矮的平房,逼仄的空间,窄窄的胡同,却充溢着烟火人情,相闻鸡犬之声,往来亲密无间。谁家养着几只鸡狗,谁家灶火膛冲哪儿开,老人、儿女做什么营生,远近有几门亲戚,日子过得如何,无不明明白白。谁家做个差样的饭食一胡同都闻得着味,左邻右舍都会尝到。孩子们走东家串西家,百家饭都没少吃,放了学家里没人,邻家就是家,亲戚来了家里锁门,钥匙对门就有。串门闲聊推门就进,脱鞋上炕与家无异。家里有个大事小情,胡同里的人总会第一时间出现。父子争执、夫妻拌嘴、邻里误会,婶子大娘老少爷儿们立马来到,一番讲道,析事明理,火气消散,雨过天晴。有了为难遭窄爬坡过坎的事,乡邻肯定施以援手。
那时办个红白喜事也难也不难,难的是缺东少西,钱不凑手,不难的是整个胡同的乡邻都会来帮忙,有人出谋划策、总理事宜,有人操持桌椅板凳、盘碗筷子,有人烧火做饭、颠勺炒菜,有人张罗待客迎来送往,有人舞文弄墨、写礼记账……众乡邻凑个份子,帮着主家把事办好,共济互助。
胡同里的烟火气息丰盛,胡同的人情生活很宜人。世事更迭,胡同里的人长大了、老去了、远行了……